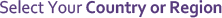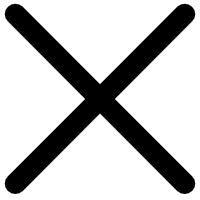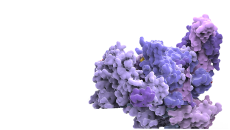[1] Syed F, Khan S, Toma M. Biology. 2023; 12(7):1026.
[2] Khurana R, Simons M, Martin JF, Zachary IC. Circulation. 2005 Sep 20;112(12):1813-24.
[3] Liu ZL, Chen HH, Zheng LL, Sun LP, Shi L.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. 2023 May 11;8(1):198.
[4] Logsdon EA, Finley SD, Popel AS, Mac Gabhann F. J Cell Mol Med. 2014 Aug;18(8):1491-508.
[5] Crivellato E. Int J Dev Biol. 2011;55(4-5):365-75.
[6] Liao YY, Chen ZY, Zhou QL, et al. Biomed Res Int. 2014;2014:872984.
[7] Deveza L, Choi J, Yang F. 2012;2(8):801-14.
[8] Al Sabti, H. J Cardiothorac Surg 2, 49 (2007).
[9] Raica M, Cimpean AM. Pharmaceuticals (Basel). 2010 Mar 11;3(3):572-599.
[10] Yun YR, Won JE, Kim HW, et al. J Tissue Eng. 2010 Nov 7;2010:218142.
[11] Khanna, Astha, et al. Encyclopedia. Web. 29 May, 2023.
[12] Nazeer MA, Karaoglu IC, Ozer O, Albayrak C, Kizilel S. APL Bioeng. 2021 Apr 5;5(2):021503.
[13] Wang Y, Zhao S. Vascular Biology of the Placenta. San Rafael (CA): Morgan & Claypool Life Sciences; 2010. Chapter 7, Angiogenic Factors.
[14] You WK, McDonald DM. BMB Rep. 2008 Dec 31;41(12):833-9.
[15] Lugano R, Ramachandran M, Dimberg A. Cell Mol Life Sci. 2020 May;77(9):1745-1770.
[16] Liao YY, Chen ZY, Wang YX, Lin Y, Yang F, Zhou QL. Biomed Res Int. 2014;2014:872984.
[17] Lin S, Zhang Q, Shao X, Zhang T, Xue C, Shi S, Zhao D, Lin Y. Cell Prolif. 2017 Dec;50(6):e12390.
[18] Dallinga MG, Habani YI, Schlingemann RO, et al. Mol Biol Rep. 2020 Apr;47(4):2561-2572.
[19] Slater T, Haywood NJ, Wheatcroft SB, et al. Cytokine Growth Factor Rev. 2019 Apr;46:28-35.
[20] Guerrero PA, McCarty JH. InTech; 2017.
[21] Veith AP, Henderson K, Spencer A, Sligar AD, Baker AB. Adv Drug Deliv Rev. 2019 Jun;146:97-125.
[22] Francavilla C, Maddaluno L, Cavallaro U. Semin Cancer Biol. 2009 Oct;19(5):298-309.
[23] Dakouane-Giudicelli M, Alfaidy N, de Mazancourt P. Biomed Res Int. 2014;2014:901941.
[24] Nan W, He Y, Wang S, Zhang Y. Front Physiol. 2023 Aug 2;14.
[25] Cavallaro U, Liebner S, Dejana E. Exp Cell Res. 2006 Mar 10;312(5):659-67.
[26] Rundhaug JE. J Cell Mol Med. 2005 Apr-Jun;9(2):267-85.
[27] Zhong S, Khalil RA. Biochem Pharmacol. 2019 Jun;164:188-204.
[28] Iragavarapu-Charyulu V, Wojcikiewicz E, Urdaneta A. Front Immunol. 2020 Mar 5;11:346.
[29] Hasan S S, Fischer A.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medicine, 2023, 13(2): a041166.
[30] Sanhueza C, Wehinger S, Castillo Bennett J, et al. Molecular cancer, 2015, 14: 1-15.
[31] Fernández JG, Rodríguez DA, Quest AF, et al. Mol Cancer. 2014 Sep 9;13:209.
[32] Cheng N, Brantley DM, Chen J. Cytokine Growth Factor Rev. 2002 Feb;13(1):75-85.
- Anti-infection抗感染
- ADC Related抗体偶联药物相关
- Apoptosis凋亡
- Autophagy自噬
- Cell Cycle/DNA Damage细胞周期/DNA 损伤
- Cytoskeleton细胞骨架
- Epigenetics表观遗传学
- GPCR/G ProteinG 蛋白偶联受体/G 蛋白
- Immunology/Inflammation免疫及炎症
- JAK/STAT SignalingJAK/STAT 信号通路
- MAPK/ERK PathwayMAPK/ERK 信号通路
- Membrane Transporter/Ion Channel跨膜转运
- Metabolic Enzyme/Protease代谢酶/蛋白酶
- Neuronal Signaling神经信号通路
- NF-κBNF-κB 信号通路
- PI3K/Akt/mTORPI3K/Akt/mTOR 信号通路
- PROTAC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
- Protein Tyrosine Kinase/RTK蛋白酪氨酸激酶
- Stem Cell/Wnt干细胞及 Wnt 通路
- TGF-beta/SmadTGF-beta/Smad 信号通路
- Vitamin D Related/Nuclear Receptor维生素 D 相关/核受体
- Others其他
Anti-infection
Apoptosis
Cell Cycle/DNA Damage
Cytoskeleton
Epigenetics
GPCR/G Protein
- 5-HT Receptor
- Adenylate Cyclase
- Adhesion G Protein-coupled Receptors (AGPCRs)
- Adrenergic Receptor
- Amylin Receptor
- Angiotensin Receptor
- Apelin Receptor (APJ)
- Arf Family GTPase
- Arrestin
- Bombesin Receptor
- Bradykinin Receptor
- Cannabinoid Receptor
- CaSR
- CCR
- CGRP Receptor
- Chemerin Receptor
- Cholecystokinin Receptor
- CRFR
- CXCR
- EBI2/GPR183
Immunology/Inflammation
Membrane Transporter/Ion Channel
Metabolic Enzyme/Protease
- 11β-HSD
- 15-PGDH
- 17β-HSD
- 3β-HSD
- 5 alpha Reductase
- Acetolactate Synthase (ALS)
- Acetyl-CoA Carboxylase
- Acetyl-CoA synthetase
- Acyltransferase
- ADAMTS
- Adiponectin Receptor
- Aldehyde Dehydrogenase (ALDH)
- Aldehyde Oxidase (AO)
- Aldose Reductase
- Amine N-methyltransferase
- Amino Acid Oxidase
- Aminoacyl-tRNA Synthetase
- Aminopeptidase
- Aminotransferases (Transaminases)
- Amylases
Neuronal Signaling
Protein Tyrosine Kinase/RTK
Stem Cell/Wnt
- 重组蛋白
- Cytokines and Growth Factors
- Immune Checkpoint Proteins
- CAR-T related Proteins
- CD Antigens
- Fc Receptors
- Receptor Proteins
- Enzymes & Regulators
- Complement System
- Ubiquitin Related Proteins
- Viral Proteins
- Biotinylated Proteins
- Fluorescent-labeled Proteins
- GMP-grade Proteins
- Animal-free Recombinant Proteins
- 重组蛋白定制
- 定制合成服务
- ADC 相关定制服务
- PROTAC 相关定制服务
- Cytokines and Growth Factors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
- Immune Checkpoint Proteins免疫检查点蛋白
- CAR-T related ProteinsCAR-T 相关蛋白
- CD AntigensCD 抗原
- Fc ReceptorsFc 受体蛋白
- Receptor Proteins受体蛋白
- Enzymes & Regulators酶和调节子
- Complement System补体系统
- Ubiquitin Related Proteins泛素相关蛋白
- Viral Proteins病毒蛋白
- Biotinylated Proteins生物素标记蛋白
- Fluorescent-labeled Proteins荧光标记蛋白
- GMP-grade ProteinsGMP 级蛋白
- Animal-free Recombinant Proteins无动物成分重组蛋白
- Others其他
- View More
CAR-T related Proteins
- CD27 Ligand/CD70
- B Cell Maturation Antigen (BCMA)
- FLK-1/VEGFR-2
- B7-H3
- CD4
- CD19
- CD27 Ligand/CD70
- CD123
- CD138/Syndecan-1
- 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 (EpCAM)
- Folate Receptor 1
- GPC-3
- Guanylate Cyclase 2C
- ErbB2/HER2
- ErbB3/HER3
- c-Met/HGFR
- MSLN
- CA-125
- ROR1
- CEACAM-5
- CD314/NKG2D
- 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
- CD319/SLAMF7
- TROP-2
- Siglec-6
- Folate Receptor alpha (FR-alpha)
- CD314/NKG2D
- Siglec-3/CD33
- CD27 Ligand/CD70
- CD138/Syndecan-1
- CD319/SLAMF7
- ErbB2/HER2
- CD138/Syndecan-1
- Nectin-4
- Siglec-3/CD33
- Carbonic Anhydrase 9 (CA IX)
- EGFR
- FLK-1/VEGFR-2
- CD7
- CD20
- Siglec-2/CD22
- CD30
- CD38
- MUC-1/CD227
CD Antigens
- T Cell CD Proteins
- B Cell CD Proteins
- NK Cell CD Proteins
- Macrophage CD Proteins
- Monocyte CD Proteins
- Stem Cell CD Proteins
- Platelet CD Proteins
- Erythrocyte CD Proteins
- Dendritic Cell CD Proteins
- Epithelial cell CD Proteins
- Endothelial cell CD Proteins
- Signal Transduction-related CD Proteins
- Cell Adhesion-related CD Proteins
Receptor Proteins
-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
- Receptor Serine/Threonine Kinases
- Receptor Tyrosine Phosphatase
- Receptor Guanylyl Cyclase Family
- Cell Adhesion Molecules (CAMs)
- G-Protein-Coupled Receptors (GPCRs)
- Nuclear Receptor Superfamily
-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
- Notch family
- Siglec
- Leukocyte Immunoglobin-like Receptors
- Killer-Cell Immunoglobulin-like Receptors
- Cytokine Receptors
Enzymes & Regulators
- Oxidoreductases (EC 1)
- Transferases (EC 2)
- Hydrolases (EC 3)
- Lyases (EC 4)
- Isomerases (EC 5)
- Ligases (EC 6)
- Translocases (EC 7)
-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
- ADAMs/ADAMTSs
- Cathepsin
- Carboxypeptidase
- Angiotensin-converting Enzymes
- Caspase
- Carbonic Anhydrase
- Serine/Threonine Kinase Proteins
- Protein Tyrosine Kinases
- Phosphatase
- Topoisomerase
- Protease Inhibitors
- Protein Kinase Inhibitor Peptide (PKI)
- Cyclin-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Proteins
- Cystatin Family